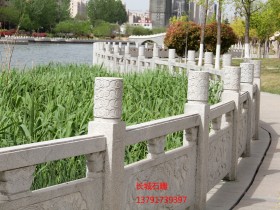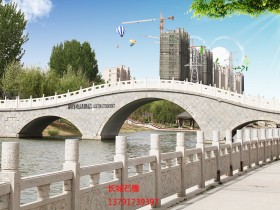- A+
射击整个栏杆
梁恒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出身于军队,以武术起家,最后转向文学为业,成为一位伟大的诗歌作家。这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诗歌和他在文人中的独特性以及他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从我看到的信息来看,辛弃疾至少用利剑杀了好几个人。他生得身材高大,从小苦练剑法。他出生在金宋乱世,对金人的入侵和蹂躏感到不满。 22岁时,他召集了数千人的起义军,后来与耿精领导的起义军合并,并担任秘书长并负责封印。有一次,叛军中发现了叛徒,他偷走了印章,准备投资黄金。辛弃疾手持利剑独自追贼两天,第三天就找回了人头。为了重拾大业,他劝耿精南下,亲自南下临安联络。没想到,没几天,他又受伤了。出使归来,部将叛乱,耿精被杀。辛大怒,跳上马,横剑而去。他率领几支骑兵冲入敌营,活捉了叛将。遂不远千里,护送他到临安讨回公道。还率万人南下归宋。说白了,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满腔大义,想要杀掉山贼,为朝廷收复失地。
但这世上的事情不可能成真。回到南方后,他立刻失去了手中的钢剑,手中只剩下一把软毛笔。他再也没有机会冲上战场,血溅衬衫,只能像龙蛇一样写字,在宣纸上流下泪水。为历史留下一连串悲惨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话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刀剑刻的。他作为战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留在了历史和自己的诗篇中。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清秋落日稼轩拍遍栏杆报国无门,依然感受到一种凛然的杀气和磅礴的力量感。比如这首名曲《破阵》:

醉时点灯看剑。我梦想着在连营里吹响号角。八百里外,部下火烧火燎,塞外传来五十弦琴声。秋天,部队上战场。马的动作迅捷,弓的弓声如霹雳般可怕。完成君王天下之事,赢得前后的声誉。不幸的事情都是徒然发生的。
我敢大胆地说,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之外,这首诗可以与之相媲美。在中国五千年的文人墨客中,很难找到另一首能与金歌之声相媲美的佳作。虽然杜甫也写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事诗人王昌龄也写道:“欲驱轻骑兵,大雪遮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者的想象、表达和描述。哪位诗人有过这样滚在刀锋上的经历呢? “飞上军舰楼”、“甩鞭飞过江”、“剑指三秦”、“西风赛马”,他的诗简直就是一本军事词典。他原本将自己的遗体许诺给国家,准备在沙漠中洒血,用马皮包裹自己的尸体。然而南渡之后,他被迫离开战场,不再有用。他像屈原一样仰望天空,像共工一样愤怒而困惑。他面江,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唯有流泪。
楚天千里秋色清,水随天行秋无边。目光远眺,献上悲愤,玉钗螺髻。夕阳西下,楼上破钟声中,一个江南游子看着吴钩,拍遍了栏杆,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也没有人来看他(《水龙歌》)
谁能理解他这样一个浪子实为亡国浪子的悲愤?这是他来到建康市赏心阁时所做的事情。这座面向古秦淮河的亭子,是历代文人雅士的鉴赏之地,而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鸣。当他痛苦地拍击栏杆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以前他是如何拍剑催马驰骋沙场的。但如今,他如果有全部的力量和野心,又能用在哪里呢?我曾特意去南京寻找辛工拍摄栏杆的地方,但人们毁掉了建筑,没有了踪迹。唯有江水悠长,流淌,如诗人的长叹,向东流去。
辛的词与其他文人的更深层次的区别在于,他的词不是用墨写的,而是用血和泪涂抹的。今天我们读他的诗,总是清晰地听到一位爱国大臣一次次的哭泣、告白;我们永远忘不了他站在夕阳下的栏杆上,睁大眼睛望着远方的画面。
辛弃疾南归后为何如此不受朝廷待见?他在一剧《戒酒》中说:“怨恨无论大小,由所爱而生;无所谓好坏,做错了就会酿成灾难。”这幅素描完美地描绘了他的政治痛苦。他因爱国而怨恨,因尽职而遭祸。他非常热爱国家、人民和朝廷。但朝廷畏惧他,惹恼他,避免重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一共生活了四十年,却闲散了近二十年。在断断续续使用的20多年里,频繁调动37次。不过,只要有上场的机会,他就会非常认真、执着地工作。本来,有碗饭吃,他就不应该做什么,但炽热的爱国心却把他全身烧焦了。 40年来,无论身在何处、担任什么职务,甚至失业时,他也不断写信、唠叨。一有机会,他就必须努力工作,训练军队,筹集资金,组织政务,总能上演好戏。就像冲到前线一样。你以为这不会让主公和苟安朝廷不高兴吗?任湖南抚平使。他原本是地方长官,却在任职期间,在江南创建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马驹,兵马雄壮。建军之初,建了军营,但碰巧连日阴雨,屋顶瓦片无法烧制。他命令长沙市民立即给每户送去20块瓦片,并立即支付现金,两天之内就筹集到了全部资金。其干练的执政风格可见一斑。后赴福建任地方官,并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和漠北虽然相距遥远,却无法隔绝他对人民的关心和复兴国家的雄心。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工作狂,但他太过分了,“过犹不及”。他最终招来了不少诽谤,甚至说他独裁、有罪。皇帝有时用他,有时废他。国家危难时,他用了几天;国家有难的时候,他用了几天;国家有难的时候,他用了几天;朝堂上有谗言,他就废了几年。这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他虽然读了很多诗书,但诗中处处用典,甚至被后人嘲笑为“丢了书包”。但直到他去世,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南宋小朝廷只想维持和平,不愿意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曰弃疾,可他五尺身躯,自幼挥枪挥剑,力如铁塔,难道有什么病吗?他心里只有一个毛病:金杯不见,月未圆,山河破碎,心不安。
玉姑台下,清澈的河水清澈见底,不少路人都流泪了。向西北望长安,山峦无数。青山遮不住,终究要东流。江琬担心我,听见山深处有鹧鸪叫。
这就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上读到的著名的“菩萨男”。他患有抑郁症。他甚至嘲笑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勇,万年家谱。你的姓氏是哪一年起的?细读“心”字,微笑听。辛苦,悲伤的味道,总是酸酸的,辛苦的。更让人觉得刺鼻,胡椒和肉桂的捣碎都能让人吐出来。世间应有的芬芳与美丽,在我家门口却找不到。 (《永远的幸福》)
你看“苦”、“酸”、“悲”、“辣”,真是五样东西。世界上有很多甜蜜的事情和野心,但为什么这些都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要么闲着,要么被调动。 1179年,由湖北调任湖南。同事送行时,他心情为难,最后以十分委婉的语气感叹自己的政治失意。这就是著名的歌曲《摸鱼》:
又可消几场风雨,春来匆匆。我珍惜漫长的春天,却又怕花开得早,更何况无数红花飘落。春天,留下来!坚曰:天涯香草无归路。怨春无声。即使屋檐上只画着蜘蛛网,日惹的柳絮也飞扬起来。这是一件长久的事情,但最好的日期却错了。莫梅曾经嫉妒过。就算花上千金买了一份如礼物般的礼物,这种感觉谁又能抱怨呢?别跳舞。若不见我,玉环飞燕都将化为尘埃。无所事事的悲伤是最痛苦的。不去一卫楼,夕阳西下,杨柳断心。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诗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论道:“肠梗阻如此令人不安,是前所未见、空前绝后的。” “阊门事件”是指汉武帝陈皇后被贬至阊门宫的事件。与这部经典相比,辛充满了忠诚、痴情,还有很多苦涩、辛苦、辛辣,真是颠覆了五味。今天读起来,每一个字都令人惊讶,让人感觉只是一滴血,一行泪。确实,古代文人的作品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哪首歌能把春色变成政治,并如此委婉而悲壮地解释政治呢?佳人相思也是老文人过度使用的题材。还有哪一首歌能如此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判善恶、抒发悲愤呢?
但南宋朝廷却让他闲置了20年。 20年来,他一直远离政治。只允许他观看,不准干涉、干涉。辛在诗中自嘲道:“大王对你有恩,请教我如何种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评价刘墉的话:“去低声歌唱,何必出名呢?”刘庸真的去找钱了。我低声唱,结果是一个纯粹的作词家和艺术家。辛与刘不同。仔细想想,他是一个喝大碗、吃大块肉、拍栏杆、高声论政的人。由于无法报国,他到赣南建造了一座带湖的别墅,以品味自己的孤独。
我非常喜欢这个湖。数千英尺的绿色圆顶展开。张先生无所事事,每天步行一千次。所有与我们结盟的鸥鹭,今日结盟之后,请不要猜测彼此的来去。无论白鹤在哪里,都要尽量和谐。折断绿浮萍,排出绿藻,挺立青苔。偷窥鱼嘲笑你疯狂的计划,困惑地举起我的杯子。废弃沼泽荒山已过,月明风清。这一夜,世间有太多的欢乐和悲伤。东岸绿荫较少,需多植柳树。 (《水条歌头》)
这一次,他真的响应了他的号召:“家轩”,要回家乡种田了。一个盛年的政治家,阅历丰富,志向远大,每天走遍山坡水边,与百姓闲聊桑葚的丰收等事情,然后在鸟儿鱼儿面前自言自语。真是……“闲愁最痛”、“此情谁能怨?”
说到辛弃疾的书写功力的深浅,无论是刀刻还是血写清秋落日稼轩拍遍栏杆报国无门,其实他的追求从来都不是成为一名诗人。郭沫若评价陈毅:“将军的本质是诗人。”对于辛弃疾来说,诗人的本质是武士,武士的本质是政治家。他的话就是政治大磨石磨出来的豆浆汁。他从武术走向文学,又从文学走向政治。他始终处于出生与进入世界的矛盾之中,遭受着被利用或被抛弃的痛苦。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谈到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只涉足政治,而不再涉足政治;他也不像白居易,在位时间长,政文兼备。他有一颗为国家、为民族,比天还大、比天还热的心;他有一种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的能量,无法抑制或耗尽。他不在乎“五斗米断腰”,也不怕流言谩骂。因此,每当局势波动时,他就忙碌又闲散,大起大落,大进大退。如果他有一些政治成就,他就会受到诽谤和抛弃;国家有难,征召任用。他亲自组织、训练军队,撰写了《美勤十篇》等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像贾谊、诸葛亮、范仲淹那样总是忧心忡忡的政治家。他就像一块铁,有时被锤打得通红,有时被扔进冷水里淬火。有人说他是继承苏东坡的豪爽豪迈之人,但苏东坡的豪爽仅限于“大江东去”和山河浩瀚。苏征正处于北宋太平盛世,没有民族仇恨和野心来炼化他的诗歌灵魂,也没有胡晨飞和金格明来增强他的诗歌力量。真正的诗人只有在重大政治事件(包括社会、国家、军事等矛盾)的挤压、扭曲、扭曲、锤炼和锤炼下,才能获得符合历史潮流的感悟,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只有受到政治之风的搅动,才能飞扬、燃烧、爆炸、启迪人们。学诗的功力在诗外,诗的功效在诗外。我们认识到艺术本身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艺术加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的诗其实属于雍容派,与柳永、李清照一样多愁善感、细腻。
我最近很烦恼,谁能可怜我呢?谁能互相理解?让我再担心一下吧。

他们都把无尽的前世今生的事抛在脑后。放在悲伤一边,却迁居酒泉。
(《丑陋的奴隶》
少年不知悲情,爱上了楼上。爱上楼上,我强迫自己表达悲伤,以便谱写新的文字。
现在我知道了所有的悲伤,我不想再说话了。我想放弃,但我说秋天很凉。
(《丑陋的奴隶》)
刘、李的感伤仅限于“手牵着手,泪眼婆娑”和“梧桐树下细雨绵绵”。然而,辛诗中那些婉约忧郁的词句,在轻盈的艺术美感中,却蕴藏着深刻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理。 。真正的诗人最善于表达普通人心中的伟大情怀和道理,能够在寂静的地方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我常常想,如果要创作一尊辛弃疾的雕像,最合适的标题就是“栏杆上到处都是照片”。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感到被遗弃和无助的感觉中度过。当权者不允许他为官,而是为他磨练思想和艺术准备了消极的环境。他被蒸过、晒过、煮过、煎过、锤炼过无数次。历史的风雨,民族的仇恨,善恶的斗争,爱恨的纠葛,知识的积累,情感的铸造,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炼,这一切都在翻滚。在他的胸口和脑海里。 、搅动,如岩浆在地壳中的翻滚、膨胀、冲击和堆积。既然这种能量无法转化为刀枪之威,也无法转化为政治政策,那就只能倾注于诗,转化为诗。他本来不想当诗人,但从政之路被堵住了,历史迫使他成为诗人。终于,他被训练到了连叹息都能写出好诗的地步。归根结底,才华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就像岩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无法成为旗杆,但依然可以成为强大的龙头手杖,价值不菲。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从“战场上秋令将士”到“秋高气爽”;从决心为国放弃病魔,到最终将其碎尸万段咀嚼,明白“辛”字的含义,再到自称“甲玄”,与欧陆结盟,辛弃疾经历了一个爱国者和一个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任何人都可以写诗吗?一个诗人,一个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诗人,谁都可以是诗人吗? “一将成名,万骸枯骨”。武将的故事,需要剑客、舞者的鲜血来书写。那么,兼具思想光彩和艺术魅力的诗人又如何呢?他的名声取决于时代的运动,就像地球大板块的碰撞一样。有时他被夹在中间,感到折磨,有时又被抛在一边,被迫冷静思考。于是,南北宋三百年的动乱,就产生了辛弃疾。
关于作者:
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著名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政治评论家。曾获全国青少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现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 我的微信
- 这是我的微信扫一扫
-

- 我的微信公众号
- 我的微信公众号扫一扫
-